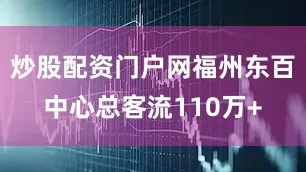张万银
20世纪50年代,国家在小兴安岭中段南麓兴建一个大型木材加工厂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,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小镇。镇上的居民大多“半工半农”:“半工”是在工厂上班,“半农”是下班后种菜。我们家奉行“近地家中宝”的原则,在房前屋后建了两个菜园。
那时候我们房前是一片坑洼不平的荒草地,经过一番芟除平整,对着屋门扎上“U”字形的篱笆,一个一分多地的小园就诞生了。
转过年,当春风又绿兴安岭的时候,春雪就知趣地悄悄融化,去滋润黑土地。然后,一畦一畦的菠菜、生菜、香菜、小白菜的嫩芽,像春天的先头部队,探头探脑地冒出来;一垄一垄的黄瓜、青椒、紫茄、西红柿经过育苗移栽,腰杆逐渐硬起来,迎风舒展青枝绿叶,见谁都点头致意。几番阳光雨露之后,小园里热闹起来,红繁绿盛,引来嗡嗡的蜂、翩翩的蝶,帮着清点蔬菜瓜果。
这个小菜园我们称它为“前园”,种的菜称为“小菜”——现拔现吃的蘸酱菜——春夏的主要菜品。俗话说东北有三缸:大酱缸、酸菜缸、腌菜缸。大酱缸就放在菜园的中央,接受阳光的爱抚,吸收植物的精华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打耙,酱就“发”了,颜色由淡黄变为金黄,满园飘散豆酱香。中午或晚上,下班的、放学的,先到菜园里薅几样水灵灵的小菜,用清水漂洗一番,舀上一碗黄豆酱,焖上一锅二米饭,农家饭就齐了。
春夏吃菜的问题解决了,可秋冬的蔬菜还没有着落。我们决定在屋后不远的地方,用课余时间创建一个“后园”,主要种秋冬吃的豆角、土豆、倭瓜、萝卜、白菜等“大菜”。
吃菜容易建园难,建后园几乎耗尽我们哥仨一个秋天的力气。选好的园址是河堤下的一片荒地,有几只白羊在啃青草。一个风日晴和的日子,我们拿着镰刀扛着镐,开进作业现场。除草、刨地、打坷垃;垒一围田坝,扎一圈篱笆……农谚说“一亩园十亩田”,可见劳动量之大。
转过年,薄薄的东风又吹来,冰凌花凌寒独自开,河面上开始跑冰排,催耕的布谷鸟叫起来。我们趁天晴把园子里的土翻耕耙平,打散晾晒,起垄下种,静待一片绿意葱茏。不知不觉地,豆角秧上架了,土豆秧开花了,倭瓜的青蔓在篱笆的脚下爬,沿途开花吹着黄喇叭。清代画家边寿民有一首写菜园的诗《瓜茄豆角》深得我心:“老屋苇间傍水滨,客来相访定知音。何须远市营兼味,只向畦边架上寻。”
“畦边架上寻”得来东北秋天的主要菜品——铁锅炖。当地有一句俗谚:“东北一大怪,上贴饼子下炖菜。”说的就是东北佳肴铁锅炖,又名“一锅出”。具体做法是:把土豆、油豆角、倭瓜放在一起炖,开锅后,锅的四周贴上发面的苞米面薄饼,大火猛炖20分钟,就饭菜齐熟。揭开锅,菜还咕嘟咕嘟冒着气泡,香味随着热气弥漫开来。豆角青绿,倭瓜淡黄,土豆修炼得没了棱角,入口即化。圆饼鲜黄香软,正面浮着一层菜油,背面带着焦黄的锅嘎巴儿,仿佛金黄的圆月。饭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桌,全家人围坐吃得满嘴油光,热气给每个人的脸上都晕染出一团嫣红。
铁锅炖吃到深秋,就要准备过冬的蔬菜了。一是收秋菜。起土豆、拔萝卜、砍白菜……该入窖的入窖,该土埋的土埋(萝卜、胡萝卜等初期是埋在深土里以防冻保鲜,待三九天再刨出来入窖)。二是晒干菜。豆角、萝卜切成丝,土豆、倭瓜切成片,西葫芦用刀将果肉旋成一整根薄薄的长条,挂在晾衣绳上,在暖阳下、金风中摇晃。三是腌咸菜腌酸菜。还未到霜降,菜园就进入老龄化社会,蔬菜的孝子贤孙——黄瓜纽儿、茄子纽儿、尖椒纽儿、豆角纽儿,等等,就被收入坛子里,在盐水中冬眠。这些坛坛罐罐只能算小兵,它们的将军是胖大粗憨的酸菜缸,有1.3米高,可腌200斤大白菜。将军统帅着列兵,排在厨房的东墙下,随时恭候主人的召唤。
黑龙江漫长的冬季冰封雪飘,经常喝大馇子粥——金黄的苞米馇子加上紫色的饭豆。大馇子粥开锅后小火慢炖两个多小时,炖得饭豆都笑开了花,就可以上桌了。大馇子粥的配菜从“四大家族”里选:咸菜、干菜、酸菜、窖藏菜。比如西葫芦干炖猪肉,那西葫芦干又韧又脆,新鲜爽口,嘎嘎香。如果再配上一碟碧绿青黄的咸菜,就更不知今夕何夕了。
以上说的是我家一年四季的蔬菜饮食史,可谓园蔬青翠粥饭香。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年代,粮食、副食凭本定量供应,家家都相同,不同的只有蔬菜。谁家种得多、种得好,谁家的生活就好,不负人生不负胃。清朝王苹有诗云:“细读农书细把瓮,且将种菜论英雄。”我们可能算不上种菜的“英雄”,但至少能算合格的“农垦战士”吧?
恒正网-什么股票配资平台安全-配资炒股开户平台-配资低息炒股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